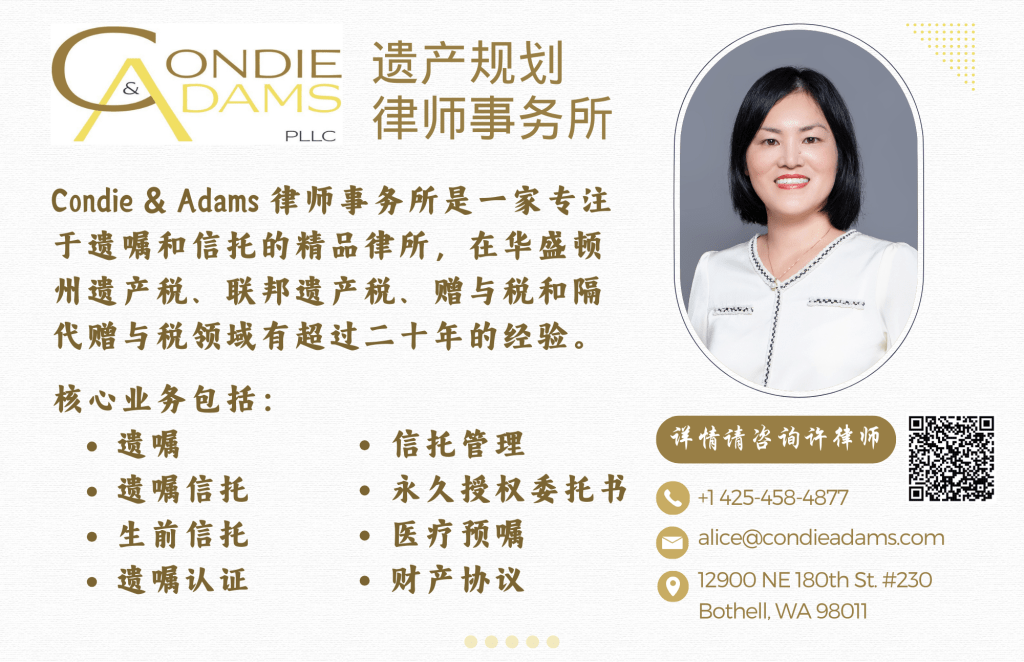文/丁学良
(丁学良是香港科技大学荣休教授,1992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,曾就职于哈佛本科生院(Harvard College),澳洲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(RSPAS,ANU)、卡內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等。)
3月两会期间关于民生的话题最多,今年最热的话题包括“青年人是弱势群体”,“2019年进大学的青年人是最弱势的”。
我的观察对这些议论提供了背景。新冠疫情前,内地一过完春节能听到许多趣事,其中之一,是“租个对象回老家过年”。没有对象的青年人(女士为主),受不了回故乡被自家长辈和邻居盘问“有对象了吗?为啥这么大年龄还没对象呀?” 为了避免烦人的盘问,有些青年就花钱雇用一个看起来挺帅的假对象,陪自己回老家过年。我问过多位,付费挺高,因为要应付很多难堪的场面。今年春节后我却听不到这类趣事了,一问,得到的多数回答是:这年头哪还有钱去雇佣假对象?找工作就够烦人了!
数据吹气减压力
对年轻人来说,找工作比找对象更要紧,这符合经济学社会学的预期。我在1月13日《信报》评论里,引用了内地2024年11月经过查询,能够得到的公开数据。数据显示,中国内地去年下半年高校应届毕业生,包括专科、本科、硕士生,全国的平均就业率56%。
评论发表后我继续向内地高校教师、管理层和职业市场研究者请教,他们教育我,那个数据极不可靠,多重原因导致许多部门或经办人,对应届毕业生的就业率数据吹气。
我对这个问题一直非常关注,原因有三。
原因之一,国际上高校教师为学生求职助力是通例。我在内地当顾问的高校的毕业生,有几位的专业是国际经贸,仍然难找到工作,即使是在深圳这样外向型经贸的基地。
原因之二是为大湾区的高教全球化(目标包括吸引东南亚的留学生来香港、深圳和广州读学位)做规划。哪些专业在未来的5至10年内有更好的就业前景,是必须慎重算计的教学资源安排的依据。在美国、欧洲与中国持续不断的经贸和技术的竞争大格局下,制造业和供应链的重新配置,必须与以人力资源的支撑为基础。香港应该成为整个东南亚甚至部分南亚地区的高教市场,外来学生付全额学费加生活费,是本港一大收入。
原因之三更宏观。所有从低收入状况成功走进中高收入倶乐部的国家或地区,高校毕业生的素质和工作状况不可忽视。判断内地经济从中等收入的水平往上攀升的进展如何,要考察许多指标,其中最关键的包括历年高校毕业生在总人口里的比例、毕业后的起步就业机会、中长期的事业发展途径(主要是25岁到55岁)。所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高校毕业生在职业市场上的轨迹,是多个社会科学专业共同研究的大课题,牵涉到本地经济结构的变迁之下教育资源的配置、教育体制的改革、专业架构的调整。
这类研究必须是前瞻的,不能等到应届毕业生已经拿到学位证书、忙着找工作的时候,才开始研究该过程中接连出现的冲突。回顾1990年代初香港在讨论走向高附加值产业的挑战时,常听到的反馈是:香港优秀的高中生多半不愿意报考科技专业,因为毕业后的就业机会和收入不理想。香港本地缺乏庞大的工业体系,获得理工科学位的毕业生要么去内地就业,要么在香港做国际贸易,比如经营科技产品的跨境供应链。那个时候香港被西方发达国家当作自由开放的贸易中心,对高科技产品的进出口限制少,所以一些理工科毕业生做跨境贸易生意兴隆。但这个形势正在变得严峻,新加坡在美国压力下严查高级芯片转口贸易的事件,是最新的警示。
从职业市场的动向反过来研究高等教育架构的改革和发展,是公共政策的一大领域。我先把近几年内地的问题摆出来,以后再讨论大湾区(就高等教育而言,香港仍然是领先的城市)的前景。
签意向书当获聘
内地毕业生的就业数据极复杂,我曾经参与的研究项目首次遇上麻烦,是2008至2009年金融海啸。内地出口拉动的产业受到负面影响,特别不利于高校毕业生。一旦就业越来越难,政府部门给高校的硬性指标压力就越来越大,就业率成为衡量一所高校办得如何的显示器之一。这么做当然有合理之处,你说贵校的教学素质优秀、实习项目扎实,但你的毕业生在职业市场上却不受欢迎,咋回事儿?如果你还不及时改革,贵校以后的招生率和新生素质就会衰减。然而,高校应对就业率日增的压力,还有其他招数,最方便的是朝统计数据里吹气。
讨论至此,我们面对的主要问题是:2024年度内地高校毕业生的整体就业率,真是公开数据所说的56%吗?两个多月来我认真请教了很多人,包括对高校教师和经济媒体人,位于京、沪、华南、东北,他们提供的资讯要点如下:
第一,“就业”的定义有严格、也有宽松的标准。愈是早年的统计数据(2009年以前),愈偏向于严格标准:愈是近年的统计数,愈是使用宽松标准。二者之间的关键区别是:前者是指应届毕业生一拿到学位,凭着此前签订的聘书立即进入工作岗位,随后领取相应的工资和福利;后者是指应届毕业生与聘用单位签订了“意向书”,该单位也可能把意向书转成正式的聘用合同即法定文件,也可能废除并不具有法律保障的意向书。若此,该毕业生只能去找下一个聘用单位。
第二,遇上经济不景气、职业市场提供的新岗位明显缩减,高校就会把毕业生的求职“意向书”充当正式聘书纳入统计数据上报。这样既使得本校在同类高校中不显得更加衰弱,也能够避免政府相关部门批评。
第三,2009年之前,许多应届毕业生的就业统计数据并不对外界封闭,研究者能够对同类高校提供的数据进行比较鉴别。由于金融风暴严重影响,新的就业岗位下滑,促使许多高校对应届毕业生的就业数据采取保守的措施。外界研究员获得大面积数据的难度愈来愈高,迫使许多研究项目只能做局部考证,拿不到大面积数据。
第四,最近几年,有些高校把应届毕业生里准备报考研究生或出国留学的,不纳入“未就业”范畴,即做小“分母”,这样就使得就业率看起来更高。条件较好的高校,院系给每个教授分配任务,让他们聘用求职失败的应届毕业生作研究助手,每人每月2000至3000元,校方拨款。所有这些做法,都是在“就业率是硬指标”的政策上或上级指令压力下,高校各级的减压措施。
报研究生非待业
第五,据有经验的几位观察者的估计,2024年应届毕业生的实际就业率大约是30%至35%范围内,不会高于40%,肯定达不到广为流传的56%。在“数据出关,关出数据”的大环境下,这类统计数据相差如此之大,并不令人意外。虽然得不到全面的可靠数据,我们不妨同时也用较低的三个就业率数据做估算,进行比较。若此,2024年总共1179万应届毕业生里,到春节前尚未找到正式工作的人大约是825万、或766万、或707万。
从2020年初到2023年初,内地都在疫情影响下。到了2023年6月毕业时,虽然不再有严格的防疫管控,社会基本恢复常态,但应届毕业生面临的职业市场与前3年相比并无显著改善。所以我也对这4年的就业状况做出估算:2020年高校毕业生870.1万;2021年903.8万;2022年1076万;2023年1158万;4年加起来4007.9万。假如平均就业率是56%,总失业人数是1763.5万。假如平均就业率是40%,总失业率人数2404.7万。假如平均就业率是35%,总失业人数2605.1万。假如平均就业率是30%,总失业人数2805.5万。
2月尾开学后我继续与内地高校教师交流,他们说,最差的高校就业率连30%也达不到,只有20%左右。班级辅导员告诉应届毕业生,找不到工作就在填表时写“灵活就业”;“碰到调查时,就说在做自媒体”。如果有些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在20%左右,以上的估算还要大幅度调整。
数量如此巨大的高校毕业生前途在哪里?他们个人及家庭当然责任最沉重。据观察,他们母校能帮到忙的地方不多。还有哪些社会机构、行政部门能出手相助?这才是目前和未来几年内地公共政策的巨大挑战。在这个问题上,暂且只能讨论到这一步,再往下就愈来愈说不清,因为没有一个主要数据容易获得,而公开能查到的全面就业数据多半不牢靠。
本篇评论试图把这个复杂领域的第一个层面尽量讲清楚,它涉及到内地经济、社会、政治、法律的交叉部位,影响大湾区的诸多项目,以及香港从内地引进人力资源的长期政策。两会期间,能发表更可靠的数据吗?